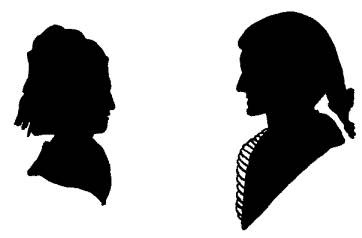楼主说“猪狗不是主体,永远是人的财富,是客体。故他们仇视贪官,热爱清官的心态可以说是因为它们畜牲的身份使他们无奈只能这样。但是人如果是这样就只能解释为智商问题了。”
“智商”这个词,很模糊。如果说是大脑的一种潜质,中国人的智商不一定就比西方人低。我听说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即使是原始部落的人类智商也和我们差不多。那么,楼主的意思又是不是指认识水平呢?像黑格尔所指出的,中国人的认识水平还比较低,还没有充分的自我意识,缺乏主体意识。这个意思也许比较接近楼主的意思。
那就谈谈我的认识。谈清官和贪官,应该先谈官和民。说清官好,贪官不好,这是缺乏反思的。不管是贪官还是清官,官和民在中国的语境中已经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了。不管是说“父母官”,还是说“为人民服务”,似乎都在暗示我们官和民是两个不同的但有密切关系的实体。君子和小人(民),很早就是两个并行的概念了。这个区别太重要了,如果承认这是两个平行的概念,那么两者的关系只能是施恩和拥戴,施暴和反抗。在这个关系中,拥有权力的始终是官,这个权力是自上而下来的。因此监督权也就不是自民而来,而是自官的最高级,皇帝,而来。自己监督自己,要不出问题,难。看看中国历史吧,虽然钱穆先生指出了中国政治是在逐步演进的,但这非质的演进掩盖不了中华帝国2000多年来该死的循环的事实。而按社会契约的说法,人的自然状态是自由的个体,为了共同的利益出让自己的权利形成契约,也就是放弃自然自由获得契约自由;如果社会契约遭到践踏,每个人就放弃协议的自由,收回其自然的自由。也就是说,最开始只有 “民”,并没有“官”和民对立,“官”是“民”选出来按照协约行使权力的。
再来说说清和贪的问题。我以为不要把官放在民的对立面,首先要看作跟民一样,他也是人,官也有七情六欲,有大多数人都会有的缺点和优点。对于一个人,你不加以有效监督的给他偌大的权力,让他手里拿着成百上千万的 RMB,你又要让他不贪,这可能吗?让别人做圣人,先想想自己能不能做到。别看咱们骂起贪官来个个似乎都是半个圣人,让你去了那个位置,我看也不定保得住不贪。反正我是不行的,给我这样的权力,又不监督我,老子第一个贪,我自认为个人品行还算中等以上。中华帝国自秦以来,大部分的官都是自民出,为什么一当了官就变了?难道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再说,一个官不贪,很难在官场立足。不贪,上上下下很多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很多老婆等着买的衣服,很多孩子等着要的玩具和男人的尊严就被清官这Y的给弄吹了,人家能不恨他吗?反正换作我,我第一个或者跳出来或者背地里骂他娘。好,你不贪,老子就脚下使畔子,叫你当不了这官。不贪,上司就怕了,这Y想干嘛,野心看来不小啊。当年李世民的爸爸李渊还是唐国公的时候,别人告他有异志,李渊知道了,赶紧养晦。我不知道邓说 “韬光养晦”是什么意思,方正这位国公爷是开始收贿赂了。做官跟做人一样,做人首先得活下来,活着就什么都有希望,像《芙蓉镇》里姜文说的,要像狗一样活着,中国人一直就是这个观点,“好死不如赖活着”,那么做官呢,也得先当下来才行啊。什么,客官你说海瑞怎么行?那我问你,张居正屁股不干净,但你说张居正的功劳大还是海瑞的大?你说海瑞不是被排挤吗?那我问你,海瑞为什么不先做上去再来一展宏图呢?你说不能以整个官僚系统腐朽来为个人的腐朽辩驳?那我问你,一堆清官就等于好的官僚系统吗?为什么清一色清官的官僚系统从来没出现过,无论中西?这只能说明这样定义下的系统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它或许将来会使合理的),因为它居然没有取得现实的力量来实现它自己。而且关键在于,个人品行问题和体制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把这个搞混,要么是认识问题,要么就是玩弄权术,故意掩盖问题。
楼主暗示中国人的“清官情结”是因为缺乏主体意识,就是自我意识的水平还不高,对“自由”这个概念的认识还很低下。这其实就是西方民主思想。这看来是主观认识问题。但是,一个中国人有,这是主观问题,许许多多中国人代代都有,这就是客观问题了。如果仅仅把人的认识归结为智商问题,那就什么都不说了,人生笨了还有什么办法。不过,既然楼主去了民主国家就改变了认识,我想我也有希望了。我想,认识是在劳动实践中形成的,人在改造(认识)对象的同时也改造(认识)了自身。一定的认识是在一定的实践中形成的。脱离了认识的实践根源,从西方搬过来概念是没有根的水。黑格尔对中国历史和哲学评价都不高,说中国只有一个人自由,又进一步指出,其实这一个人也不自由。这的确是一针见血,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我们应该寻找背后的原因,物质的、历史的原因。
而且,我们可以按黑格尔所说“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来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清官情结”,我想很早就有了,《诗》说“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大概能折射出一二来。在那个时候,这个“情结”算不算落后呢?我看不见得。马可波罗曾经赞美了中国官员的精明和廉洁,认为西方不如东方。这大概可以侧面表明,清官在中国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清官情结是有合理性的,这个情结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也曾经是世界上很先进的东西,也是有合理性的。虽然它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失去了合理性,是应该被消灭也正在被消灭的“非现实”的东西了。因此,我们不能以为现在不“合理”的东西曾经也是不“合理”的,正如我们不能“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去搞清楚这个情结曾经的合理性和现在的不合理性,它产生和现在被指责的社会根源。这个根源我认为跟中央集权有关。
华夏大地很早就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稳固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这个国家的特点就是一与多,一个皇帝和其它人。这一个人拥有天下,“家天下”,其它人什么都不拥有,所占有的都是这一个人的赐予。(中国没有私有制。)但是皇帝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大个家,于是皇帝赋予权力给官员(政府的官员是逐渐从君王家臣演变出来的),由官员来管理这个家,管理群氓。人民是没有权利的,也没有土地,(《诗》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华夏的不成文宪法。不要说地主有地,没有宪法保护的。)人民拥有的权利都是皇帝赋予的,是自上而下赋予的,而不是自下而上转让来的。在这样的社会下,产生“清官情结”是很自然的,产生“民主”思想则是很难的。没有私有制的国度产生民主思想,没有听说过。这个情结和这个社会是一致的。
这样的帝国曾经是很先进的,也是很得人心的。(想想为什么楚霸王不得人心,因为封建制已不得人心)。这个帝国的产生和它能够维持2000多年,这中间的原因太复杂了,不是我这个水平能搞清楚的,但我觉得有两个因素是产生中央集权和维持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的主要原因。这就是:治水和抵抗蛮族。
这两件事从古到今,都是要调动整个华夏民族的人力和物力来完成的。这么大的系统工程给中国带来的最重要的两个东西就是,成熟的官僚系统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抵御蛮族,从黄帝和蚩尤的斗争就开始了,现在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当然提法变了。治水,咱么可以看看大禹治水。为什么大禹之后就出现了第一个王朝?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才出现?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治水给中国人缔造了一个初步成熟的官僚系统和军队。大禹那次治水,一定是一次全国性的水灾,至少南方灾区一定到了浙江,据说杭州的名字和大禹有关,大禹据说死在绍兴,越人据说就是大禹的后裔。这么大的灾害,就是98洪水估计也比不上,在那个时代要治理这样大的灾害,不锻炼出一个庞大训练有素的官僚系统来开展这个系统工程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个官僚系统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才能快速有效的调动一切资源。另外,再来想想在98抗洪中的主力军是谁?是解放军。那么反过来推,在那个时代,进行抗洪的群众们在抗洪过程中很有可能被训练的十分有组织,这样的人群很容易投入战争。在地理知识上,经过这次抗洪,庞大的华夏版图一定第一次开始清晰了,关于华夏的地理知识一定获得了一次飞跃,这些知识对于一个要中央集权的国家可是相当重要啊。在政治上,经过这次治水,大禹的功绩和威望,恐怕只有黄帝才能和他相提并论了。这一切,都为中国政治的早熟准备了最重要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和民众的二元关系很容易建立起来,哪怕以前的权力是自下而上赋予的,现在一切权力都收归了那个皇帝,然后再由他来统一安排,分配。另外提一提后稷也是有必要的,治水的根本目的除了生存,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灌溉。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业知识、技术和工具的改进对于提高亩产量是十分重要的,而亩产量直接影响人口,人口多少是衡量国家富强的极端重要的指标。周的祖先是后稷,后稷就是农官。周是一个重视祖先的民族,后稷的后代也差不多都是农业技术的专家。后来的公刘似乎也是。也就是说,君王还担当着生产指导专家的地位,这是关乎民生的事。另外,灌溉是农业的命根。但是灌溉除了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人事问题。比如《平凡的世界》就讲了一件上游县把水库一关,下游就没水喝了的事。因此君王还得居中调节各种人事矛盾。
所以在中国谈西方民主,谈私有制,先不说抵抗外敌的问题,首先就得考虑如何解决水的问题。治水的问题牵扯很多,最敏感的就是地方和中央的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谈不来。
说了咱们的情结,大致也提提西方民主吧。西方民主的思想产生于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但追本溯源是希腊文明。相比中华的大河文明,希腊文明主要的是海洋文明,有很强的商业味道。所以谈古希腊就会发现,古希腊的地域是变化的,西到西班牙,东到小亚细亚,北到黑海北岸,南到埃及,都在某个时期曾经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商业社会中,私有制和法制就比较容易建立起来。商人多,势力大,确立私有制是比较容易的,私有制确立,基于私有制的法制就容易确立起来,因为是基于私有制的,所以比较能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民权的概念就容易建立了。中国战国也出现过发达的商业现象,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这条路呢?我想这还是和咱们这个大河大江以及因此早就建立起来的政治思想有关。而希腊能发展出民主的概念,也和它的城邦制紧密关联。这些问题很大了,我没有这个能耐,只不过提出自己的猜测罢了。
反正呢,楼主揭示的“情结”问题和指出的认识上的缺陷,我都是赞成的,但对于“病态”一说不敢苟同。凡事皆有因。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细究起来,实在不是个小问题,要牵扯出大问题,是个要考虑中国历史很多方面,要对比东西差异才能给出满意答案的。希望有识之士能出来一解小子之惑。